创新药历史中,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一起标志事件,成为行业转变的分水岭。
从恒瑞的仿制药,贝达的埃克替尼,到微芯的西达本胺。现在,则是越来越多创新药企,以License out的方式,争夺海外市场。
“以前我们是自己玩儿,没有进军全球的机会。现在已有七八家企业与海外合作,三家早期产品和四五家成熟产品,再过几年可能就不止这些了。”王印祥认为,未来10年,会有越来越多药企出海。
中国创新药License out热潮始于2020年。除了加科思的SHP2抑制剂、信达生物的双特异性抗体和细胞治疗产品,后来者目前还有荣昌生物、天境生物、基石药业、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也在此队列中。
“单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制药企业市值大幅下调,就是因为国内市场的空间已经到头了。”这是二级市场的判断。
与微芯生物创始人鲁先平一样,曾创立贝达药业的王印祥,也是20年前最早一批创新药拓荒者之一。区别在于,拿着600万美元启动资金的鲁先平,举起了中国第一款First in Class创新药的大旗,贝达药业则迎来了中国第一款Me too药的诞生。

△ 加科思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印祥
如今,那个年代的拓荒者仍活跃在业内的已经不多。王印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但贝达药业不是他的终点,2015年他创立加科思新药研发,锁定了有全球市场潜力的First in Class。
创新药人的幸存者
有着城南“药谷”之称的亦庄,20年前还是北京南郊有名的“练车场”。王印祥“二次创业”成立的加科思,就坐落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因贝达药业肺癌靶向药“埃克替尼”名声鹊起的王印祥,未曾想到,2000年前后那段“暗流涌动”的历史,昭示着中国创新药的开端。
1997年,彭朝晖回国,成立赛百诺,研发成功全球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次年,罗永章回国,创立麦德津,我国首个具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抗肿瘤新药“恩度”,由此诞生。
如今已淡出创新药领域的彭朝晖和罗永章,打响了中国创新药研发的第一枪,掀起了国内创新药研发的新浪潮。
五年后,在北京西城一间30平方米的实验室内,毕业于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王印祥,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首次创业——贝达药业。
“融资”,是王印祥的第一道坎。
“那时候创业条件非常艰苦,全国都没有几家VC投资公司,除了IDG资本等几家华尔街的VC,而且它们多投向了互联网行业。”王印祥介绍。他甚至开玩笑说,现在光亦庄的VC就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国的总和。
早期生物医药企业的“第一桶启动资金”,靠的都是非专业投资人。彭朝晖的赛百诺、罗永章的麦德津,都是在政府资助下启动。
缺钱,少政策,没有适合药物研发的基础设备,贝达药业的早期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租下的30平方米的实验室,丁列明等几位朋友投资的几百万元启动资金,河北廊坊用水泥搭建的氢加压反应釜……在这种“小米加步枪”的环境下,王印祥完成了新药的“雏形”。
新药进入临床Ⅰ期试验阶段后,却在北京协和医院吃了闭门羹。与医院伦理委员会主任单渊东教授一个半小时的对谈,王印祥才打开了医院临床的大门。
2009年1月,即将在27家医院同时启动三期临床试验时,又遭遇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意外打击,项目投资被迫暂停,贝达药业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幸运的是,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的1500万元,礼来亚洲基金的500万美元,以及大股东分头筹措的资金,帮贝达熬过了这次危机。
两年后,顺利完成临床试验的“埃克替尼”获批上市,成为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治疗晚期肺癌的靶向抗癌药,也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儿。
顺势而为的“二次创业”
事实上,受限于早期凋敝的行业生态,贝达药业是以Me too药物起家。
“当时我们都是在条件很简陋的状态下成立的,没有现代化的公司构架和专业的风投资本,只能做一些跟踪式创新,所谓的Me too药。”王印祥坦承。
Me too药是在现有药物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创新,对已有药物结构进行改良,获得更佳的临床效果或者差异化的市场定位。除了贝达药业药业的埃克替尼,另两个Me too药恒瑞的艾瑞昔布、君实的PD-1抗体,也较为知名。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医药行业。而此时,药明康德、泰格等中国CRO公司正蓄势待发。美国不少药企和大批CRO公司,纷纷前往中国寻找“过冬”的商机。
同一时期,施一公、饶毅等明星学者回国,带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人才的回国潮。
如果说彭朝晖、罗永章,以及王印祥、鲁先平和丁列明等,是中国第一批创新药的代表人物,2008年之后,信达、君实、再鼎等后来者的崛起,则代表了国内创新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很明显跟2000年初第一批创业者不一样了。他们的产品虽然主要针对中国市场,还是在做Me too或者Fast follow这种跟踪式创新,但起步就以亿元计,有国际专业资本VC的介入。”
国内资本的涌入,抬高行业起点的同时,也拉升了整体成本。到2015年,一线城市的高端研发人员待遇,已经跟美国持平。
王印祥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细节现象,预示着创新药未来的道路。
“拿全球的成本,做占全球不到10%的中国市场,这个逻辑就不对。创新药跟消费品不一样,必须突围到全球。”
如今的贝达,已从最初几十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上千人的规模企业,但整个中国创新药态势已发生巨大变化,License in、Me too同质化竞争惨烈,Fast Follow式的创新红利即将见底,继续走老路,“中国市场就玩不下去了。”
王印祥决定,做First in Class,并且是Global first in class。
然而,当公司具备一定规模后,战略调整阻力重重。“转型要考虑各种因素,需要一套全新的机制。比如,做全球创需要新的团队和新的机制。打破旧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在经营层面非常困难的事情。”王印祥说。
2015年,王印祥启动“二次创业”,成立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与首次创业几百万元捉襟见肘的起步资金相比,二次创业之初,就获得了礼来亚洲基金、启明创投、晟德、高瓴资本等明星资本的加盟。
这一次,王印祥也坚定了做原创药的决心。
挑战难成药靶点
“格列卫”的问世,是王印祥那一代创新药人,屡屡提及的改写了肿瘤药历史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长达60年的时间里,肿瘤治疗处于化疗药阶段,针对肿瘤细胞发展迅速这一特点,“宁可错杀、也不放过”地将人体内生长速度过快的细胞全部杀死。于是,往往伴随着患者要承受脱发、呕吐、造血抑制等强烈且痛苦的副作用。
直到2001年,首个靶向抗癌药物“格列卫”诞生。此后20年间,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远超前60年的突飞猛进,诞生了数以百计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
对患者来说,更多的选择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对创新药企来说,则意味着白热化的竞争过后,可成药的靶点已经所剩无几。
“必须再进一步,挑战过去技术做不到的难成药靶点。”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以及患者需求的考虑,王印祥都无意再趟入同质化的红海。
SHP2抑制剂(JAB-3068和JAB-3312),是加科思首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全新First in class产品。2015年,加科思成立不久,便盯上了这一难成药靶点的潜力,比业内对该靶点的关注整整早了三年。
提前三年,可谓占尽先机。加科思的SHIP2抑制剂,仅次于跨国药企诺华,是全球第二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同类产品。其后,Revelution和Relay相继加入赛道,但已无法撼动稳居第一梯队的加科思。
目前,加科思基于难成药靶点的另两大项目,KRAS G12C抑制剂和BET抑制剂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主攻难成药靶点的巨大风险,是阻挡本土创新药企再向前一步的最大路障。尽管2020年被业界认为是本土药企转向Frist in Class的元年。
王印祥对此早有准备。
一款新药从酝酿到诞生,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从分子水平验证、细胞水平验证,到动物试验,最后才是人体试验,是一个微观走向宏观的过程。
每一阶段的验证,企业在满足药监局控制标准之上,有一个“可松可紧”的范畴,技术风险控制便隐藏在其中。比如,在动物试验阶段,肿瘤抑制率达到可以进入人体试验的标准,但如果将标准进一步提高,成功机率就更大。在每一步都对标最高要求,未来失败的风险就越低。
新药永远和风险相伴,用尽科学上的技术手段,也无法保证100%的人体成功率。商业风险控制是最后一道需拧紧的阀门。
2020年5月底,在SHP2抑制剂尚处于研发早期阶段时,加科思通过License out的方式将其海外权益授权艾伯维,不仅是为了借船出海,也是出于稀释商业风险的考虑。
这笔交易,让加科思在当年便将4500万美元的首付款收入囊中。未来,8.1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也将陆续进账,海外销售额两位数分成的纯利润,也给了王印祥,出征海外的底气。
“出海”之后
全球市场,是王印祥口中的高频词。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行业需求。在王印祥看来,仿制药、Me too、Fast Follow的时代终结之后,First in Class必须立足全球。
市场规模,决定了药企的销售上限。IQVIA曾统计,2020年中国处方药市场规模约1.2万亿元,剔除中成药和仿制药会骤降至700亿元。而据Evaluate分析,全球处方药市场2020年达到9040亿美元,约5.8万亿元。
“中国最大的制药公司,几十个产品一年总销售300亿左右,也就是50多亿美元。而艾伯维一个肿瘤产品,在全球就有90亿美元的销售额。我们几十个产品的销售额,不到艾伯维一个肿瘤产品的一半。”
集采“灵魂砍价”、医保降价压力、内卷的同质化竞争,也逼迫本土药企“出海”。走出去,就是五倍甚至十倍的市场。
2017年,南京传奇生物“牵手”杨森,共同开发和商业化CAR-T细胞产品;2020年,天境生物将CD-47单抗的海外权益授权艾伯维;同一年,加科思也与艾伯维达成合作协议。这三款产品均为早期授权,高达10亿美元的转让额,也不再是早年药企为延续资金链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百济、信达、君实等企业,将其PD-1海外商业化权益授权诺华、礼来、Coherus等跨国药企,掀起了中国成熟产品“出海”的热情。

这是中国创新药,有能力走向全球的转折点。然而,海外市场,并非人人可及。
在王印祥看来,争取出海机会,企业立项时要有学界认可的科学基础;同时,项目要中美双报;最重要的是,同一个项目必须能突进全球前三。“即使你的项目很好,但全球有十几家公司在做,基本上也没有机会License out。”
IQVIA曾统计,在药效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全球首个上市的药物能争得64%的市场占有率,其次为25%。第三名之后的入场者,能分到的全球市场微乎其微,除非取得突破性的明显优势。
“出海”意味着进入全球竞争,技术壁垒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在本土时代行将终结的前夜,已领先多数同行的王印祥,仍在未雨绸缪。
First in Class仍然在过去30年生物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寻找难成药靶点上的突破,但这段历史也将很快过去。“慢慢这些都成药了,以后连靶点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发现,如果没有Discover的能力,连创新的门槛都摸不着。”
王印祥预计,“原始发现”的时代可能会在10年后初露端倪。
在业内,不少全球知名学者开始将更多精力投注到原始发现。“虽然原始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商业的必然成功。但这种趋势、这种投入、这种努力非常重要,他们是在为未来铺路。”
陈思丨撰稿
季敏华|责编
尊重原创版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本文来源:八点健闻 作者:小编 免责声明: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医药行”认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与我们联系
 八点健闻
八点健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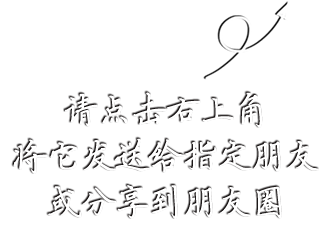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