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声音·责任|赵超:鼓励同行兼并、优胜劣汰,中药注射剂不宜一棍子打死
多位与会的代表、委员认为,此次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医药事业所存在的短板却仍然不容忽视。不管是备受争议的中药注射剂,还是亟待提升的中医诊疗力量,都需要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关注。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的作...全文>>
新冠肺炎不是第一次,也必定不是最后一次。疫情结束之后,如何将对重大疫情的应对体系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中?政府、企业、行业分别应该做哪些事情?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各个行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关键的时刻展现出来以人为本的魄力和决断能力以及在疫情防控中的组织动员能力令人欣喜,我们医药行业表现也可圈可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能力不足,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医疗、医药政策的空白。如何填补这一空白?
新冠肺炎不是第一次,也必定不是最后一次。疫情结束之后,如何将对重大疫情的应对体系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中?政府、企业、行业分别应该做哪些事情?
几乎所有与会代表和委员都提到了改革或重塑中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清明提到:“要全面构建多方参与、信息透明、迅速响应、产业协同、保障有力的立体防控体系,这是应时、应势、应世之举。”
于清明认为,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管理链条上很多关键环节存在漏洞,比如新冠肺炎初期信息不畅、响应不快、准备不足;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直报系统在疫情初期并没有发挥好前哨作用;专家对疫情预判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够清晰;地方政府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及时发布风险预警等。
此外,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储备方面的落后和不足,不仅投入不足,各级物资储备也没有形成标准,应急物资调配不及时、不系统,应急物流指挥能力不足、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等。
也不止一位与会代表和委员提到了疾控体系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数据显示我国疾控队伍2018年是18.8万人,2003年是20.8万,队伍正在缩减。另外疾控系统存在专业人才短缺、设施设备老化、培训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
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何琳今年已经第三次就疾控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提出议案。她认为,一定要将稳定疾控队伍落实到可操作性层面。第一是调整疾控体系的投入,要有可操作性;第二可以参照广东省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把疾控人员纳入公务员的管理,从工资待遇还有职业发展方面都能够有所提高。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凌峰也提到,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上到天、横到边、纵到底”的疫情防控体系。所谓“上到天”能够有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汇报疫情的信息汇报机制。“横到边”是要从口岸卫生检疫一直到社区卫生防疫都要波及,“纵到底”是建立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的公共卫生体系,相当于当年的计划生育体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董小平认为应该赋予疾控中心一定的行政权。现在的疾控中心没有信息发布的权利,这肯定会滞后疫情向社会有效公布的速度。其次,现在的疾控系统是属地化管理,上级疾控部门对下级疾控部门没有任何领导权,他建议可以在战时适当赋予上级疾控部门一定的行政权,使其有调配资源的能力。
此外,董小平建议,应该打通疾控跟医院信息联通。疾控中心是一个前哨部门,也是专业的技术部门,如果掌握信息不充分,与疫情的这场“战争”肯定没法打。

从左至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董小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凌峰、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清明、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何琳
公共卫生体系不是仅包括疾控系统,而是囊括了社会各界、各个机构和行业的国民健康“防御”机构。疾控体系之外,医疗、医药等体系的配套也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发现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我国一个短板是,全国很多千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都没有一个真正像样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而上海在2003年建立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004年投入使用,有五百亩的土地,在这次疫情中间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朱同玉建议应该在全国各大(尤其在千万人以上的)城市中间,布局国家应急医学或者是战略储备中心。平时这个中心可以做一般性的、一千到两千床位的综合性医院,在战时能够迅速扩展到五千张床左右的规模。而这个医院应该具备三个属性:第一有超强的机动能力,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扩展到几千张床位的水平;第二应该是科学中心,应该有一些战略储备物资或技术,在破解病原体、疫苗和药物研发方面有所作为;第三有超强的综合能力,传染病医院不单是简单的治疗传染病,还应该具备比如ECMO等治疗技术。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唐旭东则看到全国各省市的三甲中医院及央属三甲中医院中没有像样的专科传染病防治医院。他认为应该在各省市及央属医院里面建立一所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治的专科医院,挂靠在某三甲医院作为第二院区进一步完善。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认为,在完善公卫体系之外,还应该加强完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包括疫情和灾情)下的危机干预。就像本次疫情迅速蔓延,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好,导致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舆论给民众带来恐慌情绪。因此加强科普教育、做好情绪疏导非常重要。
葛均波建议,第一应该加强整个社会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防控和防御能力;第二建立权威的信息源,通过官方媒体、协会、学会等传播科学、透明、真实可信的信息,着力提高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则聚焦在如何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眼科医务人员感染了28人,3人因新冠肺炎去世,这引起了中国眼科界乃至国际眼科界的关注。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和中华预防医学会迅速出台了防控指南,现在已经被国际眼科理事会在国际眼科医生防护中采用。这充分展示了学术组织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中,往往合并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死亡率更高,这也提示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注意到,传染病防控中统一实施,分层管理、网格化负责、责任到户、责任到人、有指标、有考核的特点,正是心血管疾病控制所需要的。如果能将传染病防控经验应用到慢病管理,可以对慢病管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延伸阅读:正大天晴降价,这家药企撑不住了!就地解散河南销售团队,带量采购“蝴蝶效应”来了
带量采购引发的“蝴蝶效应”正在呈现。随着带量采购扩大化,裁员、公司调整架构等会越来越集中爆发。 近日有业内自媒体爆料,称某国内药企因为产品挂网时间延后,叠上疫情和同品竞争的影响,导致河南市场开发和销售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公司和大区预期目标,因...全文>>
从左至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唐旭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
疫情爆发时,除了一些老药新用的特效药,最被人期望的就是研发出新冠疫苗。但对企业来说,疫苗研发周期长、投入高,一旦疫情结束,疫苗可能面临没有市场的窘境。如何平衡疫苗研发投入和回报,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康希诺生物朱涛表示,我国现在有几个疫苗已经到了二期临床,但由于现在新冠疫情发病率低,很难开展三期临床,但疫情在秋天回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必须早一点把三期有效性试验做出来,控制疫情。其次,国家应该加强应急技术能力。比如载体疫苗平台、mRNA疫苗平台、DNA疫苗平台等,这种平台技术有利于国家快速响应新发传染病。
另外,朱涛提到,病毒无国界。中国疫苗出国参加国际临床研究是有必要的,但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出国做疫苗尤其是创新疫苗临床研究还较少,希望国家能够统一组织,协调申办方、研究者、CRO、分析实验室等参与到国际临床研究中去。
从左至右: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资深顾问冯丹龙、康熙诺生物首席科学官朱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
华兰生物安康则指出中国医疗应急生产储备仍然薄弱,且并没有很好解决常态和应急之间的矛盾。以疫苗生产为例,2009年甲流爆发时政府向10家企业下达了疫苗生产计划,共795批,15000剂疫苗,但甲流过后疫苗需求量不足产能的1/5。安康建议,应设立国家专项应急征用资金,考虑补偿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响应应急做出贡献的企业充分的经济保障。
安康还表示,应加快对新冠疫苗规范化生产车间的审批。新冠疫苗研发进展备受关注,其灭活、研发、生产应该在P3级安全实验室和车间进行。但我国目前仍有疫苗生产企业没有P3级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因此加快对p3级疫苗生产车间的审批和验收事关重大。
辉瑞制药冯丹龙提议促进老龄人口疫苗接种。冯丹龙表示,我国已经快速进入老年化社会,在这次疫情中老年人是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她建议通过开展老龄人口的疫苗接种,并提高疫苗整体的接种水平和大众的普及教育,从而实现疾病预防关口的前移,相应降低医疗资源的使用。同时,加快老年人专属疫苗的审批审评,加速相关疫苗的研发上市。
延伸阅读:E药经理人对话曾光:疾控如何改革,不应该是医改的一部分
如果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算起,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流行了4个多月。疫情首先在中国流行,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话题,截至5月16日,中国已经累计确诊8万多人,全球累计确诊457万人以上,而欧美国家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曾光认为,中国公共卫生基础薄弱,且...全文>>
本文来源:E药经理人 作者:E药经理人
免责声明: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医药行”认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与我们联系



 E药经理人
E药经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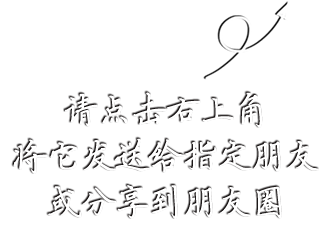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