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z_popeye
「刚刚 29 床家属把你换药的过程全录下来了。」
胆胰外科医生程薇(化名)正在换药室处理用过的器械,听见紧随而来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小一个设备,看着还挺专业,不知道他们录这个要干嘛。」
这个消息被程薇的大脑迅速处理成一种警报信号,瞬间,她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脑海里一帧一帧过着刚才的操作细节。「我很担心有什么地方出现疏漏。」
所幸,上万次的重复动作在她身上几乎留下了肌肉记忆,在确认自己的操作无误后,随之而来的是恼怒和无奈。
「我感觉自己就根本没被尊重,」回忆起那次经历,程薇这样说,「我觉得自己对工作已经尽心尽责了,但人家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信任我。」
气愤中,程薇再次返回病房,试图让患者和家属删掉刚才的录像,但家属似乎没能理解程薇的用意。「我当时可能语气也不太好,说了几句就吵了起来。」程薇说,患者和家属还质问她,如果不是心虚,为什么要急着删录像。
为了避免投诉带来更大的麻烦,程薇最终用退让平息了这场风波。有高年资的医生安慰程薇说,这样的事情临床上太常见不过,多经历几次就好了。
但程薇的困惑依旧没有被解答。「你走在大街上随便被人拍照录像,也会觉得生气,觉得被冒犯吧。」「为什么随便给医生拍照录像,大家就认为是没问题的呢?」
录音背后,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
程薇的经历并非个例。
丁香园论坛上,就曾有站友发帖求助:一个上午门诊,被两个人录了音,三个人录了像,该怎么办?而在丁香园一次对 2700 名医护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高达 86.3% 的医生都有过被患者拍摄录音的经历。

被拍摄的医生中 70.7% 选择拒绝
图源:丁香调查
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当属广州「录音门」。
2011 年,一名 1 岁多的小患者因重症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因为病情严重,小患者立即被送进 ICU 上了呼吸机。
但患者的父亲却对医生的做法存有疑惑:「孩子进来时活蹦乱跳,怎么一下子就要进重症监护室?」
不信任的种子就此埋下,这位父亲要求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全程录音,对医生诊断和往来电话也录了音。「毕竟是嘴上说的东西,我要对孩子负责,所以就做了录音。」
在经过媒体报道后,这一事件迅速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讨论。与此同时,家属的行为和舆论关注也给医疗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事医生曾在采访中表示,此事过后,不愿再做临床。
「干这行快 30 年了,但像这么强的无力感,确实很少有。」
在当时的新闻评论区里,意见相悖的两方泾渭分明:站在患者角度的人认为,这是普通群众面对医学难题时的无奈之举,合情合理,但不少医生也直言:「只要你录音,我就明确摊牌,你的病我治不了,请另请高明。」
当录音录像被患者和家属用来作为一重「保险」的时候,它清晰地展露出了医患之间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自身权益受到实际威胁,我们该如何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
「偷录」内容可以作为证据吗?
面对录音录像的患者,绝大多数医生都觉得反感和排斥,也有人表达了态度鲜明的拒绝。

图源:丁香园论坛
但这种拒绝实际上收效甚微:当患者开始录音录像的时候,医生们可能根本还没有察觉。
这些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是否会侵害医生的合法权益?
来自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的张永泉律师认为,如果录音录像主要围绕着医生的工作进行,表现了医生应尽的诊疗义务,那么,通常很难认定侵犯到医生的隐私,或威胁到医生的名誉。
「一般来说,患者录音录像的目的主要是记录信息,以防自己记错、记漏医生说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双方很少因此发生纠纷。」张永泉律师说,依照以往经验,一旦录音录像被用做重要证据,那多半意味着医患双方出现了诊疗上的分歧,「医生的口述内容可能和书面记载或患者的理解之间出现了差异。」
那么。在出现纠纷,诉诸公堂的时候,录音录像可以被用做证据吗?
「如果录音录像中可以表现出,医生对此是知情的,存在争议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张永泉律师说,「问题主要集中在未经允许的『偷录』上。」
想要作为证据使用,录音录像首先需要符合证据的三个关键属性:真实性、相关性、合法性。
首先要看,录音录像的地点是否在公共的诊疗区域,比如诊室、病房、护士站,而并非侵入到医生的私人生活空间记录。其次要考虑,这份录音录像能否客观地反映医患双方的身份。最后要确认,整个录音录像的内容是否围绕着诊疗过程展开,记载的内容是否清晰真实准确,是否经过了断章取义的剪辑或者拼接。
「只要能够整体流畅地反映事实,符合证据的关键属性,录音录像都可以被法庭作为证据采纳。」
从「书面同意」到「明确同意」
今年 5 月,《民法典》诞生。其中一处重要改动,就是将医学告知中的「书面同意」改为「明确同意」。

「在之前的一些纠纷中,告知书上或许有签字,但患者可能没有看,或看不懂告知书的内容。」
张永泉律师介绍了一起发生在沈阳的医疗纠纷案:在这起案件中,医院出具了有患者按压指纹的知情同意书,称自己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但在患者的描述中,他被叫到护士站,把手指按在采集指纹的机器上,电脑里随机就一次性打出了数十份带有他指纹的告知书,但告知书上的内容,医生却没有详细讲解。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像这样把告知义务变成『走个过场』的情况确实存在。」张永泉律师认为,民法典新规实际上对医疗告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局限于书面形式,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我们不能用一张签字来证明患者已经知情,需要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说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
显然,录音录像作为证据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患者的录音录像行为,医生又该怎么做?
有丁香园论坛战友表示,自己越来越能「心平气和」地对待患者的录音要求。「我会坦然地告诉他,不必偷录,可以正大光明地公开录音录像。」而在遇到一些复杂病例时,也有医生会主动向患者建议:「我要说的东西比较多,你最好录下来,以免记错。」
张永泉律师建议,当录音录像发生时,医生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言行一致」:「尽量减少书面记录和口头告知的内容差异,不刻意地简略告知内容,也不刻意去诱导或误导患者,只要做到这些,就不用担心患者录音录像。」
医患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去年 7 月,山西省卫健委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活动」,鼓励患者采取「随手拍、及时拍」的方式举报投诉。但「录音录像」本身就是一个医患之间的敏感话题,在这种背景下,「随手拍」的举报方式显然会进一步加深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山西省卫健委网站截图
而一些医生为了尽可能记录事实真相,选择未雨绸缪地给自己的工作录音存档,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实际操作上,这种自发的「反录」行为不仅更添一重工作压力,录音录像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
张永泉律师介绍说,他在给一些医院进行医疗安全讲座时,时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医院应该设立专门的谈话室。
「专业的谈话室应该配备监控摄像和录音设备,在保证患者知情的前提下,完整记录告知和谈话的内容。」张永泉律师说,目前北京等地的医院已经开始为此投入精力。「很多医生也学会和习惯去使用谈话室。如果进行了比较重要的谈话,还可以向医院申请保存这段记录。」
除了谈话室之外,不少医院也在推动监控系统的完善,尽全力服务于医院的每一个角落,但这样的利好举措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
去年 2 月,一位女患者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受心电图检查时,意外发现墙面上安有监控摄像,正对体检床。患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质疑监控合理性,最终选择报警处理。

港大深圳医院心电图室监控摄像
图源:南方都市报
如何在设立监控的同时保护患者隐私?张永泉律师认为,在大厅走廊等公共区域设置监控一般不存在争议,但诊室能不能设立监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些进行问诊、开药、病历书写的诊室,布局比较公开,人员随意出入,可以认为是公共区域;但如果在一些需要进行体检、超声、影像学检查的地方,或妇产科等特殊诊室设置监控,就可能存在侵犯患者隐私的风险。
18 年 9 月,滴滴出行推出网约车全程录音功能时,也曾遭受到侵犯隐私的质疑。对此,滴滴的处理办法是,在录音前告知乘客和司机,并将录音加密保存至官方平台:如果行程中无差评、无投诉,已经上传的录音会在 7 天后自动删除;只有在出现投诉或纠纷的情况下,录音资料才可能被调取,并需要在调取前获得乘客授权。
滴滴的经验或许也可以给到我们参考,随着操作和设备的逐步完善,录音录像应该成为一种对医生和患者都有利的双面保护。(策划:gyouza)
致谢:本文经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张永泉律师 专业审核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资料:
[1]丁香调查《一个上午门诊,我被 5 个患者拍摄录音:医院里无处不在的偷拍》
[2]羊城晚报《穗「录音门」引热议,省卫生厅副厅长:谁来化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 ifanr《滴滴开启全程录音功能,真的能让悲剧不再重演吗?》
[5]南方都市报《女患者露胸检查见摄像头对着自己,港大深圳医院整改并道歉》
[6]山西省卫健委《山西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行动》
本文来源:丁香园 作者:丁香园 DXY 免责声明: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医药行”认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与我们联系
 丁香园
丁香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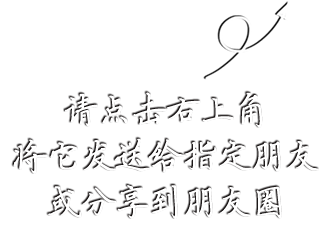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