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就在国内Biotech还沉浸在大额BD频发、港股重新开闸的热闹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Biotech却在经历一场劫难。

图1.今年已倒闭的20家Biotech(数据来源:Fierce Biotech,动脉网制图)
近日,《Fierce Biotech》发布了一份年度特殊报告,记录了今年以来全球生物科技领域的“阵亡名单”——截至11月1日,2025年共有16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式关停,另有3家濒临破产,挣扎在生死边缘。而就在该报告发布一周后,Arena BioWorks也正式宣布关停,从而将今年倒下的Biotech数量刚好增加至20家。
尽管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但其实这批Biotech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比如全球首家专注铁死亡药物研发的Kojin Therapeutics,它曾被美国化学会评为“2021年度最值得关注的十家初创公司”;另外还有Lyndra Therapeutics,它本身就出自名门,分拆自MIT的Robert Langer教授团队,创立以来融资已到E轮,并且临床也已开展到III期;最后要提到的是Hookipa Pharma,它由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于2020年联合创立,先后与吉利德、罗氏等大药企进行过多次商务合作。
虽然生物制药行业本来就是九死一生,但当昔日星光熠熠的Biotech逐一被市场出清,还是让从业者心头一紧。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才是压垮这批Biotech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失败案例”,生物医药行业又揭示了怎样的生产法则与发展逻辑?这值得每一位医药人警醒与反思!
破产清算 or 强制下线,原因为何?
虽然这20家Biotech最终的结局是相同的,但是其退场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先说主动,大多是因为资金链断裂,难以继续运营,主动选择破产清算及时止损。以专注于抗体偶联药物研发的Vincerx Pharma为例,截至2025年2月,其银行账户只有390万美元,这显然撑不到第二季度,于是在今年4月正式开启了结业清算程序。Seelos Therapeutics同样如此,根据破产申请文件显示,Seelos现有资产约856万美元,但负债高达约2873万美元,公司已无法偿还到期债务,遂主动申请技术性破产,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然后是被动,这也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上市公司,当股价跌至1美元以下时会被强制退市,比如Viracta Therapeutics,因未达到纳斯达克每股1美元的*要求被摘牌,不得不黯然关闭。另一种则是股东基于战略调整强制要求企业下线,以Third Harmonic Bio为例,虽然其一直在尝试通过并购整合来缓解危机,但投资者早已没了耐心,直接施压要求其关闭业务,把现金归还给股东。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Biotech最终被放弃了呢?通过对今年倒下的20家Biotech进行分析,动脉网总结了以下三点:
*点当然是管线质量薄弱,包括临床数据欠佳、研发进展缓慢、商业化路径模糊以及市场落地难度大等。以Oncternal Therapeutics为例,作为一家专注于癌症创新疗法的生命科技企业,其拥有三条成熟管线,分别是一款靶向ROR1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Zilovertamab、全球*公布临床数据的ROR1 CAR-T ONCT-808以及一款双作用雄激素受体抑制剂ONCT-534,但在一年时间内,三条管线全部被砍掉。
据悉,*被放弃的是Zilovertamab,虽然其已进入Ⅲ期临床,但此时的商业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考虑到市场竞争力,不得不放弃优先级,将现有现金流投入到ONCT-808和ONCT-534的临床进展。不过这并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2023年12月,Oncternal报告ONCT-808临床发生1起死亡案例,与之相关的临床开发很快被宣告停止;ONCT-534在针对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I期临床试验中数据同样堪忧,20名患者中未观察到显著疗效,最高剂量组更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3例中2例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最终迫使企业于2024年9月终止该管线研发。三大核心项目全数折戟,使得Oncternal股价一路暴跌,最终于2025年3月自愿从纳斯达克退市。
第二点关键性原因是“疯狂科学”,即一些Biotech虽然勇于挑战医学前沿,但面临研发难度大且市场不确定性强等困境,一旦资金耗尽,梦想很快就会随之破灭。以专注长效口服制剂开发的Lyndra Therapeutics为例,其拥有一款精神分裂症药物LYN-005,并在Ⅲ期临床试验中效果良好:五周治疗期内,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保持稳定,症状未出现恶化。但就在Lyndra 踌躇满志推进下一轮研发时,其融资接连失败,最后不得不止步。
对此,MIT药物递送研究所主任Robert Langer认为导火索是Lyndra走得太快了,“胃滞留技术更适合无法通过化学修饰实现口服的生物药,但当前行业更倾向先解决分子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Lyndra的技术价值或许会在5-10年后生物口服药遇到物理极限时重新被重视,但现阶段确实陷入“太早创新”的典型困境。不过即便如此,这些技术尝试仍对后续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疯狂科学”还体现在人才配置上。以全球首家专注铁死亡药物研发的Kojin Therapeutics为例,从2021年到2023年,Kojin的管理团队多以科学家为主,缺少具有药物开发全链条实战经验的人才,这就使得公司常常陷入技术*主义,优先追求科学突破,从而忽视实际的临床和商业需求,以及融资节奏和现金流控制。虽然其后续补进前ARIAD Pharmaceuticals创始人Harvey Berger博士担任公司CEO,但为时已晚,此时Kojin仅剩下2300万美元资产和10名左右员工,显然已无翻盘的可能。
最后一点关键因素则体现在整个医药行业投资逻辑的变化,不再沉迷于宏大叙事,而是更关注确定性结果,这使得一些风险较高且落地难度大的Biotech很难再融资。典型代表就是HC Bioscience,其曾被武田等明星资本和大药厂看重,并在2024年5月的ASGCT大会上宣布临床前数据,预计2025年年初申报临床,然而才过去半年多,公司就已彻底停摆。这并非没有原因,据悉,在HC Bioscience关于囊性纤维化的临床前研究中,还面临跨物种和脱靶问题,这分别涉及lncRNA靶向药物和tRNA蛋白编辑的挑战,而这两类技术都处于“高科学风险+高资本消耗”的交汇点,并不符合当前生物制药行业的投资逻辑。
对此,某美元基金负责人谈到,“现在对于Biotech的概念验证,市场的包容度可能在逐步降低,技术验证的失败,可能就意味着公司的破产倒闭,而放在HC Bioscience上,技术的复杂性导致概念验证很难成功,这使得未来Biotech公司在立项初期可能更注重技术的可行性问题。”
裁员、砍管线、被并购,Biotech如何“断臂求生”?
在一份调研中显示,有超过95%的Biotech都至少将自己的生存周期延长了2-3年。这意味着,Biotech为了活下去,实际上都在拼命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并寄希望于在现金流枯竭前杀出一条“血”路。
那么,这些“救命稻草”具体指什么呢?
首先*步就是裁员。以Carisma Therapeutics为例,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持续精简人员之后,其最后只剩下6人,对此,Carisma在官网中写道,“我们认为这6人是评估战略选项并实施有序退出所必需的”。另外一个典型代表是Viracta Therapeutics,在关键临床失败之后,其在2024年先后进行两次裁员,一次裁了23%,另一次裁掉42%的员工。

图2.2022-2025年美国生物制药行业一季度裁员情况(图源:Fierce Biotech)
根据《Fierce Biotech》裁员追踪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球生物制药行业已发生190轮裁员,逼近2024年全年192轮的总量,按此速率,生物制药行业全年裁员轮次将达252轮,较2024年激增27%。由此可见,在融资困难、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成本控制压力加剧的背景下,通过裁员来削减支出已成为众多Biotech的*选择。
裁员之后,第二步就是开始砍管线。以老牌企业ADC Therapeutics为例,其基于PBD二聚体毒性弹头技术,开发了相当丰富的PBD-ADC管线,覆盖了CD19、CD25、CD22、AXL、KAAG1等靶点,但到2025年5月,其只剩下CD19这一个“独苗”,这也是ADC Therapeutics*一款商业化产品。尽管截至2025年一季度,ADC Therapeutics现金及其等价物仍有1.947亿美元,但为了延长现金跑道,其也不得不只留下最后一条管线。
近年来,Biotech砍管线已愈发平常,一方面是因为管线本身质量不行,包括临床数据不佳或者市场竞争力小等,砍掉才能及时止损;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一些资金相对紧张的Biotech来说,精简管线才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潜力的产品上面,就比如Viracta Therapeutics,其砍掉几乎所有管线,将公司的未来全部押注在Nana-val这一个产品上。
如果前两条路还走不通,“断臂求生”的最后一步就是拼命寻求外部合作,主要是BD和收并购等。以Vincerx Pharma为例,为了达成与Oqory的反向合并协议,其进行了裁员重组,公司管理层全部大换血,但最后合作并未达成。很快,Vincerx也找到了另外一家合并目标QumulusAI,双方在2025年3月18日达成不具有约束力的合并协议,但这次的合并交易黄的更快,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终止了,而就在这次合作失败后,Vincerx立即就开启了结业清算程序。
据悉,今年已倒下的20家Biotech几乎都有与大药企合作的经历,但大多都已失败告终,这主要还是因为管线竞争力不够以及自身糟糕的财务状况,尤其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合作很容易被终止,而一旦被放弃,就相当于直接宣告了Biotech的“死刑”。以NextRNA Therapeutics为例,因未能按预期达成与拜耳合作中的关键里程碑,导致本可延长公司资金存续期的款项未能到位,最终让这家公司折戟沉沙。
整体来看,从最初的裁员到砍管线,再到最后的卖“子”求生,这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Biotech都希望通过收缩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但很多时候,这些动作更像是亡羊补牢,真正能逆袭翻盘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在风口褪去之后悄然离场。毕竟当一艘船已经千疮百孔的时候,即便再怎么努力,最终的结局还是沉没了。
热闹背后,中国Biotech应该居安思危
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生物制药IPO数量降至为零,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这反应了当前美国生物制药市场的恶劣程度。相比于美国,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在BD大爆发和港股市场回暖的推动下,当前正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总额61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77%,占全球同期交易总额的39%。
不过,在这看似热闹的背后,危机仍然存在。
一方面是体现在过度依赖BD上面,对于一些管线相对单一的Biotech来说,一旦合作终止,将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会直接中断核心产品的后续开发与商业化路径,甚至还可能引发融资困难、估值缩水与团队动荡等深层次问题。

图3.国内生物制药领域2023年年中到期的各研发阶段里程碑事件达成情况(图源:研发客)
根据SRS ACQUIOM统计,2023年我国创新药里程碑达成率仅为22%,并且阶段越往后,达成率越低,而在经过这两年疯狂的BD热潮之后,国产Biotech里程碑达成率还将继续下降,届时将会引发一系列合作终止、资金链断裂、估值崩塌与行业洗牌的连锁反应,给不少Biotech带来致命一击。
另一方面则是老生常谈的商业化难题,绝大多数医药企业当前仍处于亏损局面,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研发投入与市场收入失衡;另一种则是尚未形成“自我输血”能力,完全依赖外部融资。在更加追求稳定现金流和市场确定性的当下,这一批入不敷出的Biotech极有可能陷入“越创新越亏损”的恶性循环,最后被市场所淘汰。
事实上,Biotech陨落是常态,寒冬则是按下了加速键,而在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之中,生物医药领域的生存逻辑已愈发清晰——拼的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和管线,还有后续的融资和盈利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 参考资料:
1.《The 2025 Biotech Graveyard》——Fierce Biotech;
2.《美国“药谷”困境与中国机遇:全球生物制药格局的深度调整与战略转向》——华尔街透视;
3.《医药裁员潮终止日》——药事纵横。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动脉网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
本文来源:投资界 作者:小编 免责声明: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医药行”认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与我们联系
 投资界
投资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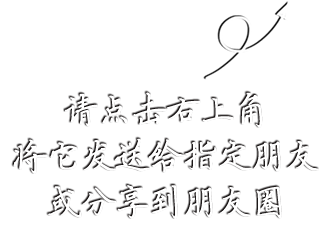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我们沟通的很顺畅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电话已拨通,无人接听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